三、悖論
(一) 何謂心理異常?
該如何確定一個人的精神真的有問題?就像前面文化取向提到的,某些「現象」在某些文化中,並不會被認為是「異常」,但在其他文化中,卻是嚇死人的疾病。例如台灣流行的乩童神靈上身,可能就會被西方社會認為是顛顯發作,儘管這在台灣卻是再平凡不過的事情。事實上,心理學界對於「正常」、「異常」,有過諸多討論,以下是一些關於「心理異常作為疾病」的論辯。
1. 反精神醫學運動
1960 年代以降,學術界出現一波由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厄文・高夫曼 (Ervin Goffman)、大衛・羅森漢恩 (David Rosenhan)、羅納德・連恩 (R.D. Laing)、湯瑪士・薩斯 (Thomas Szasz) 等人領首的「反精神醫學運動」。此運動具有強烈的解構精神,試圖反省精神醫學的客觀性與可信性。
反精神醫學運動對「正常」與「異常」的界定標準提出疑問,認為精神疾病的成因、觀感、甚至存在本身都是社會與文化建構之下的產物。這類學者大多相信:由於不同的社會文化對正常與異常的劃分不一,人的心靈或精神不同於身體,並不存在一客觀而標準的「健康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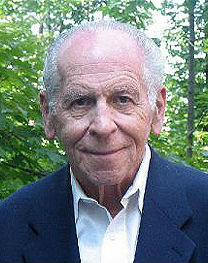
「精神疾病的存在與巫術的存在同樣『真實』」 — 湯瑪士・薩斯
薩斯在《精神疾病的神話》中主張精神疾病不同於肉體疾病,無法藉由實質的器官功能失調得知或確認。認為人們只是貪圖方便而將不符合社會標準的想法、情緒與行為歸因於「精神疾病」一由,而展現這些想法、情緒與行為的人則成為「精神疾病患者」,需要被治療以回應社會的期待。然而薩斯認為任何想法、情緒或行為在社會、道德、法律介入之前,都是中性而同等的。換言之,人們對任一想法、情緒或行為的「評價」都是社會文化建構之下的結果。由於社會文化有時空的限制與差異,任何評價想法、情緒、行為異常或正常的標準都是主觀而不穩固的。
薩斯更進一步主張,那些被社會歸類於精神疾病的行為並不是真實的疾病,而是一種「方便的神話」:人們創造出精神疾病以解釋「生存本質的困難」,正如同人們創造出巫術信仰以解釋生活中無法理解的痛苦。並提出一全新的視角看待「精神疾病」,主張應停止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與想法病態化,而應視其為個體對於生存的痛苦與自我的一種表現方式。

「一旦一個人被標定為『變態』,人們便傾向於用其後出現的行為證明這種判斷」 — 大衛・羅森漢恩
1973 年,大衛・羅森漢恩醫生受羅納德・連恩博士啟發,在美國各州進行其著名的羅森漢恩實驗。根據實驗結果撰寫《精神病房裡的正常人》一文,攻擊偏見與環境對於精神診斷與治療的影響。羅森漢恩認為此實驗結果不僅證明正常與異常的區分主觀而難以界定,更證明了診斷者或觀察者的判斷受預期心理及偏見影響甚巨。換言之,一旦觀察者為主體貼上「異常」的標籤,其後無論主體的行為多符合「正常」的標準,觀察者都會以偏頗的眼光看待,甚至不惜扭曲該行為,以合理化之前所下的判斷。
羅森漢恩認為此種自我合理化並不源於低落的專業能力或道德,而是由於正常與異常間本就存在重疊而模糊的灰色地帶。最後,羅森漢恩聲稱一對象「異常」、「瘋狂」、「憂鬱」、「神經質」、「精神分裂」等都是空洞而無意義的。治療師不應滿足麻木於爲患者的行爲、痛苦套上一空洞的病名,而應直接而誠實的面對個體患者的行為、痛苦以及這些行為、痛苦的根源。
英國 BBC 拍攝的紀錄片「到底誰瘋了」,其實也在探究這些問題。把正常人和瘋子關在一起,來驗證:到底誰瘋了。
2. 判定標準反思
德國精神學家與哲學家 Marco Stier 在《精神疾病評定的先訂標準》一文討論現代人對於反精神醫學運動的探討與反思。認為即使人的一切思考與行動皆能對應到腦的生理活動,精神醫學也絕不能被簡化為純生理、純科學的層次。Stier 在文中詳細討論了五種與精神醫學重度相關的價值判斷標準,並說明這些標準都帶有主觀想法而不具共通性或客觀性。
理性準則
理性分為理論層次 (邏輯性判斷) 與應用層次 (實用性判斷) :若一人明知 a > b 且 b > c,卻做出 a < c 的結論,可稱此人不具邏輯性判斷能力,在理論層次上可以達到完全的客觀;而若一人將資訊寫在吐司上吃掉,相信這樣就能牢記吐司上的資訊,則稱此人不具實用性判斷能力,但我們判斷此實用性時,難免帶入了主觀想法「吃吐司和資訊記憶無關」,而沒辦法達到完全客觀。
道德準則
這裡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理解:DSM 在討論 B 群人格疾患時,以「此類人格傾向於欺騙、缺乏同理心或操弄他人」作為定義,這會導致一個問題:欺騙和缺乏同理心理應是一種行為陳述,不帶有褒貶的意味,但DSM卻將之標記為「疾患」,代表DSM透過普世的道德標準,將此類行為認定為一種缺陷;Stier 在此也引述 Louis Charland 的論述:「使一人不再憂鬱與使一人不再欺騙,這兩者間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可以被視為一種治療,但後者卻是道德的改造。」以上的例子說明了精神疾病的劃分與治療並不完全是為了主體本身,而多少包含了增進社會安穩等公共目的。因此單純生物性的討論精神疾病,絕對是有其限制性的。
傷害準則
每個人對於傷害的認知與瞭解並不相同:何種程度應被稱作傷害,又何種傷害需要治療,這些標準並非是完全客觀的。Stier 強調,並不只有精神傷害不具客觀性或價值評斷,即使是肉體的傷害也需要主觀價值的介入才能真正成為「傷害」,只不過人們對於肉體層次的傷害有較為相同的標準,精神層次的標準則較會依個人、社會、文化等而產生差距。
文化準則
精神疾病評定的過程複雜且涉及各種不同的價值標準,這些標準間並沒有清楚的界限,而是相互交疊與影響的。文化對於精神疾病評定的影響尤其廣泛,實際而言,上述三則準則都與文化影響有所關連;若要討論文化與精神醫學在四個不同面向的相關性,則分別有文化與精神疾病的成因、文化與精神疾病的診斷、文化與精神疾病的個別經驗,與文化與精神疾病的觀感。
解釋準則
以不同角度觀察精神醫學,則將得到非常不同的結果,例如:選擇以弗洛伊德心理動力論的角度切入的研究者,自然會與選擇以生物醫學角度切入的研究者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因此早在選擇解釋角度時,就已有價值評斷的介入了,而且同時也不可忘記每種解釋都難免有各自的盲點與限制,所以在解釋的時候,要慎選最適當的解釋方式,不然可能會得出完全不正確的解釋結果。
此外,Stier 同時針對非理性病態化的主觀性提出兩個論點:門檻相對論和相對標準論。門檻相對論指出病態非理性的門檻是模糊、主觀而人為的,舉例而言,日常生活中經常充滿各種非理性的情緒或行為,比如貪念、嫉妒、憤怒、歧視等,這些情緒或行為都難以控制且具有傷害性,卻都不被視為精神疾病,這說明了行為或情緒的非理性並不先天屬於病態的展現,而是經過社會的價值選擇而被病態化或非病態化的。
相對標準論解釋了羅森漢恩實驗,聲明預期心理會影響判斷結果,若治療師在診斷前就先假設主體不具備判斷能力,在診斷過程中就有可能不自覺地以較高的標準檢視主體的判斷能力,於是一般而言可以被容忍的非理性行為在此便有可能被視為一病態的徵狀。
最後必須強調,以上這些論述,無論是反精神醫學運動或是對於判定標準的反思,都不是以證明精神疾病不存在為目的;精神疾病確實存在,由精神疾病導致的痛苦與傷害也絕對存在。然而,若一味地探討精神疾病的生物性病因,卻忽略了精神疾病的主觀性與社會性,此門醫學終將面臨許多難以解釋的困境。無可否認的,人的思考行為與人對行為的判斷都具有濃重的主觀性與社會性,因此即使思考與行為都可以對應到腦部的生理活動,精神醫學永遠也不應被視為客觀的純科學。
